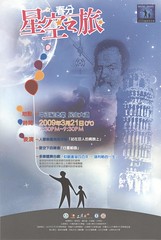周一(23日),參加了臺北文學季《在校園,文學讀字行走-校園文學扎根講座》系列中的第一場:「文學地景及文學地圖」,在台大文學院演講廳,由劉克襄先生和鍾文音女士主講。

會想去聽,是前一陣子看到文建會出版的《閱讀文學地景‧散文篇》,搜羅了諸多文學家描寫臺灣各地的作品,縱橫全台。有描繪住地的記事,有漂泊浪蕩之作,也有遊山玩水的隨筆。總之,號稱為臺灣第一套最完整的、最深入的地誌文學選集,和單純的旅遊文學是有不同。而這場演講的題名和這本書又有一些雷同,所以就去聽了。
然而,兩位作家的文學地景又是何種風光,文學地圖又要怎麼描繪呢?在各自抒發的時段,兩人分別以各自的作品,就書寫主題來談論自己的文學地景。劉克襄:自然書寫、鄉鎮書寫;鍾文音:書寫的地景、愛情的的地景、懷舊與消逝的地景和散佈的地景。
劉克襄以鳥類書寫開始,關注的題材也很有個人風格,長期都著重在鳥類的部份,慢慢推展到其他自然、生態、步道,所以他說他的第一個文學地圖是「自然書寫」。他以自然的撞擊來產生創作的主題,而不像其他作家靠著閱讀而得。
演講中提到的第一本書《風鳥皮諾查》是鳥類自述的小說,再來《旅鳥的驛站-淡水河下游的四季觀察》以報導文學的體例,描寫了關渡平原的生態,最後促成了關渡自然公園的成立。第三本《小綠山之歌》是自己在家附近臺北第二殯儀館後方的小山頭,做了一整年的觀察而寫的。他每天六點到十點到小綠山上,坐在池塘邊的樹幹上,觀察一隻命名為小英的鳥。這時候他開始體悟到「自然不是在遠方,而是在住家附近的地方」。本以為這樣的題材並不會吸引太多人,沒想到在2007年,因為建商要開發第二殯儀館後方的土地,而讓在地民眾發起「搶救中埔山」的活動。這個長期觀察而得的作品,突然有了意義。如同催生關渡自然公園,他的書寫常常不知不覺有其價值。
而他在寫《臺灣舊路踏查記》時,除了去探查高山步道,還可以不斷地旅行、觀察和創作。在尋找適合生活的家園之外,從遠方的探險,慢慢回到郊山,把郊山變得像家山,最後發現自然其實離人不遠,而開展出另一個文學地圖「鄉鎮書寫」。

自然寫作者,除了自然本身的路線外,還要有內涵。用自然觀察的方式,來寫鄉鎮和聚落。用描述植物、環境來勾勒人物的個性。例如描寫一個農家的個性,會從庭園花草的種植,或是居家周遭的植栽來展現。所以自然作家是現實的,不是超脫塵世的,和社會有結合。所以他幫南投跑水里到埔里的客運車子拍照,是一輛頭凸凸的老式大客車,他會去注意三合院內醃漬醬菜的醬缸,也會沒事誇讚老太太這麼年輕就搬到山裡住,用生活的語言和在地人搭訕,想辦法創造聊天。所以他寫了《迷路一天,在小鎮》。然而同自然書寫一樣,也是要回到自己。所以他寫了《失落的蔬果》。把臺灣曾經有被當作食物的四百種植物,挑了一百種來寫。這個寫作流程非常有趣:採集、畫畫、洗淨、料理、吃、寫吃的經驗。
到這邊劉先生告一段落,換鍾小姐來闡述自己的地景。他說如果日劇「在世界的中心,呼喊愛情」,那麼劉先生是呼喊鳥類、蕨類......。身為一位女性作家,他以比較黑暗面的角度來看傷痕寫傷痕。從他生活的時空脈絡,分為:
- 書寫的地景:故鄉雲林、青春臺北;
- 愛情的地景:花蓮東海岸回到西海岸;
- 懷舊與消逝的地景、散佈的地景:河的左岸與右岸,遊晃的淡水與定居的八里
和劉先生男性強調探險不同,他著重在女性內心的刻畫,還有家鄉的器皿、物件的描繪,用影像般的文字來寫家族史。所以一些比較深沉、內心的東西,才會被顯露出來。像是他寫看到母親背上的衣服有一個一個的小洞,就知道是去廟裡參拜,被香頭燒穿而來的。母親為何要去進香,就是在家族中得照顧家人,祈求平安的責任壓迫而致。他把鄉村中,每一個女性視作一個充滿故事的島嶼,所以有了第一本著作《女島紀事》。
再來他談了一些都市中的地景,以他居住的淡水河左岸為例,他寫了《在河左岸》,三重、蘆洲那些從中南部北上打拼的親戚,對他來說就是一幅台北的地圖。台北的地名,會帶出他散居在各地的親戚。這些底層的庶民,是城市的一部分。而一些流鶯、遊民,或是各種藏污納垢的東西,才造就出一個大都會。一些情慾的東西,包含在他的《艷歌行》中。他認為一個城市如果沒有這些東西,那也就搆不上大都會的程度。
當然,他也不是不看自然山川,不過他用了實地踏察的另一種方式,靠美術繪畫,來遊歷整個臺灣,所以他有了《台灣美術山川行旅圖》。這就是另外擴展寫作地圖的另一個方法。劉克襄在之後也誇讚,這種看風景的手段,有時候還可以看到不同的細節,也讓他感到趣味十足。
兩種不同的寫作地圖,但是都和生活有關,所以產生的對話非常有趣。
劉問鍾是如何看待像他這樣老往外跑的人,這種淨看社會光明面,充滿正義感的人,書寫出像是反共文學呼籲大家熱愛自然的作品的人?鍾說:這種題材,不是自己擅長的,所以得藏拙,多寫就是暴露自己的無知,像劉這樣可以走進自然的人,作品知識性當然會比較濃厚。而他寫的自然,則是人和自然的互動,例如農人與莊稼,或是寫淡水河跳河的人、垃圾的淤積、稠滯的流水。自然書寫像是左派的人,站在前線,有其非得看到遠方和走過去的宿命。而寫人文、愛情的人,因為競爭者眾,所以只好更加發揮想像力了!
鍾問劉在這麼大量的寫作下,都不會被婚姻、愛情的黑暗吞噬對自然的熱愛嗎?都沒有被現實而壓迫嗎?劉則簡單的帶過,他說:可能是因為男性作家本來就比較單純吧,自己很單純的生活,並不會很容易就被改變。所以在愛情、內心方面的題材,掌握得就不如女作家好。不過要是讓他來寫動物的情慾,反而又變得很簡單了。
一方面,好像是人文愛情與自然山川的對話,另一方面,又像是男女的觀點大不同。兩人的對談並沒有機鋒相對,有種互相了解、恍然大悟的快感,不過再細寫下去就過於瑣碎了。最後我問了鍾:在閱讀了那些自然作家的描述後,真正走進自然的感覺又是什麼?然後再問劉:對自然的千變萬化,應該是了然於胸,那麼要怎樣可以每次都對這些變化有所感受?
鍾說:雖然作家待在室內的時間很多,但是總是有出走的欲望。原本用想像力來描寫的世界,在真正看到後,還是會大受震撼。
劉說:他喜歡和楊照一樣,在踏查中抓歷史、看故事,開始寫作前學建築、自然,有知識再寫,把知識消化為文學。另外在作品中,有點寓言,寫起來才更有趣味。
繼上週六有場音樂與科學的饗宴,這場文學的分享,讓我對未來的寫作路線,又更有了一點方向。